我的憂鬱症症狀加重了。
我怕出意外,最近都不敢一個人待在家裡,一個人待著就容易陷入糟糕的情緒中,盡可能在咖啡廳完成工作,把所有精神都投入課程裡,約親朋好友吃飯,把所有零碎時間填滿……
第三期的課程就在這樣渾渾噩噩的狀態裡結束了。
我看得出許多人的精神狀態改變,變得更有自信,思考更正面,但那些課程在我身上似乎毫無效果。
結束課程後有一場隆重的結業典禮,每個人都獲頒不同名稱的獎狀,最優秀改變最多的同學在台上分享,助教們為所有人獻上花束,祝福他們未來一帆風順。
林品睿也傳訊息祝賀我完成課程,並向我道歉,他出差不在台灣,無法和我一起慶祝結業。
這沒什麼,我簡短回了感謝,同學們正在約會後聚餐,我正想參一腳,用聚餐當作這心靈成長課的句號,就被助教叫住了。
「屈過庭,請過來一下。」助教喊了包括我在內的五個人,我是最後一個,助教說:「請跟我來,導師想和你們談話。」
「導師有什麼事嗎要交代嗎?」我問。
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」助教沒解釋太多。
那是一間小小的導師辦公室,助教關上門就離開了,房間裡除了我們五人,就只有兩位導師——安琪菈跟錢大鑫。
安琪菈僅帶過生命之船的課程,卻仍然帶給所有人極深的印象。錢大鑫出現的次數較多一些,但也只出現六次,以科技業公司高階主管,拉格斯心靈成長學苑成功學員身份演講。三階段的課程中有無數外聘來的導師,這兩位專屬拉格斯學苑的導師雖然安排的課程不多,但地位崇高,我曾見過有助教在走廊對他們兩位行禮致意,在這年代、在台灣這個地方出現這樣的行為很特殊。
「恭喜大家結業!」錢大鑫鼓掌,露出讚許的笑容,說:「你們都是被選中的人。」
大家受氣氛感染,也輕鬆地笑了起來。
選中的人?什麼意思?我不懂現在是什麼狀況。
「選中的人?」一個西裝筆挺的傢伙比我先問出口。
我知道他,他叫王海威,在貿易公司工作,壓力大到禿頭,乾脆把頭髮剃個精光,偶而戴上墨鏡就頗有黑社會的架勢。
安琪菈靠坐在辦公桌上,雙手抱胸,以迷人的笑容回答:「沒錯!你們是特別的人,擁有資質成為拉格斯靈修會的成員。」
「拉格斯靈修會是什麼?」王海威又問。
錢大鑫問:「你們有聽過國外的共濟會、錫安會嗎?」
錢大鑫沒有等我們回答,他直接解釋共濟會、錫安會是什麼。
簡單來說,他們就是隸屬於基督教的秘密結社,從中古世紀至今,為全人類的進步付出一切。共濟會和錫安會很常出現在影視作品中,為人所知。但大多數人不知道這個世界擁有許多神秘的知識,仍舊以口耳相傳的方式秘密傳承,比如說在英國保存了魔法的薔薇十字會。
「拉格斯靈修會由我們的神聖導師KAKOGA先生,也就是水主川導師創立,他掌握了世界的真諦,擁有神奇的力量,你可以想像那是一種超能力,雖然神聖導師的力量用超能力來形容太膚淺了。」
這些話聽起來比扯鈴還扯。
王海威眼底露出興奮地光芒,他情緒激動地問:「我也可以掌握超能力嗎?」
錢大鑫說:「當然可以!每個人都可修得獨特的法門,讓我們現在就去道場舉行入會儀式吧!」
他的提議實在突然,我還沒想好要怎麼告辭離開,另一個穿著粉色洋裝的女孩子先小聲說,「但是我剛才說好要和其他同學一起去吃飯……」
她左看右看,我正要聲援她,就被錢大鑫高聲打斷:「你在開什麼玩笑,比起和那些沒有資質,不能參加靈修會的人胡混,快點去到場進行入會儀式更重要吧!」
王海威說:「沒錯,這是難得的機會,怎麼可以錯過!」
好吧。
只是去參觀一下。
✠
一台九人座的休旅車連同司機把我們載到鄰近郊區的別墅,那棟別墅非常漂亮,還有一座漂亮的游泳池。
我們在客廳裡坐了一會兒,穿著黑斗篷覆蓋全身的人送來熱茶。
所有人都喝了熱茶,看過水主川導師在水上行走的影片,水主川導師能夠掌控水,拉格斯就是盧恩符文「水」的發音,水主川導師是天上聖主,他可以引領我們追尋自我,成就自我。
太荒謬了。
沒想到拉格斯心靈成長學苑的核心是這種不知所謂的宗教,我竟然被騙了。
我想立刻離開,可是這裡是荒郊野外,我只能等對方佈教結束,開車載我們離開。
影片大約十五分鐘,等影片播放完畢,我們被帶進靜室,所有人都穿著黑斗篷、戴著面具,氣氛詭譎。
只有坐在高台上的水主川導師、安琪菈和錢大鑫露出他們的面容,黑斗篷們吟唱著奇異的音節,牆上插著燭台,蠟火搖曳晃動。
穿著粉色洋裝的女同學勉強扯了一個笑容問:「我們也有斗篷和面具嗎?」
「會有的。」安琪菈回答。
漸漸的燭光燃燒得越來越劇烈,形體扭曲變化成火炬,原本如同耳語般的吟唱變得震耳欲聾。
真奇怪啊。
這個世界的樣子,變得十分陌生。
✠
攝影機穩定的運作著,喝下添加迷幻藥物熱茶的人捧著頭癡癡地笑或流淚,彷彿看見了奇蹟,抑或望見地獄。屈過庭在藥性的影響下,跪在地上哀嚎慟哭。
沒有人知道他們看見了什麼,也沒人關心他們看見什麼,這些黑斗篷還有重要的任務需要完成。
他們為這群迷途羔羊脫光身上的衣物,教導他們發誓。
一位黑斗篷負責一名赤裸的新人,輔助新人直立的站在攝影機前,一字一句復述入會的宣誓。
「拉格斯靈修會至高無上。
我將登上天階,以拯救匱乏的靈魂。
我將潛入海底,以探尋生命的真相。
我將付出所有,以換得至高的榮耀。
我簽下十億年的契約,以證忠誠。」
✠
我不確定過了多久,醒來的時候我趴在木地板上,從落地窗往外看出去,天漸漸地亮了,從深藍色轉為薰衣草紫,漸漸的越來越亮,橘黃色的太陽出來了。
天亮了,碧藍的天空就像碧藍的海水。
我錯了。
我早就該離開,現在已經晚了,太晚了。
我是最早醒的那個,只從木地板爬起來就花掉我全身的力氣,頭一下下抽疼,就像過往我換新藥——我的醫生會因應不同情況的憂鬱症狀調整藥物劑量或種類——適應不良的狀態。
過量的違禁藥物……是毒品嗎?
有點像迷幻藥的症狀,但我從未服用過迷幻藥。
回憶昨日,最後的清醒停留在喝下熱茶後,觀看比起靈修宣傳更像魔術師表演,水主川導師在水上行走的影片……
然後呢?
「屈過庭同學?」背後傳來女孩子怯生生的呼喚。
是我們五人中唯一的女孩子程至臻,她也醒了。
程至臻攏著身上唯一的布料,一件黑色天鵝絨斗篷,縮到靠牆的位置,害怕地問:「怎麼回事?」
我們來時穿的衣服都不見了,連內褲也不例外,只隨便套著一身黑斗篷,涼颼颼空落落的,讓人心慌。
「我不知道。」
我試圖從周遭環境找到線索,從大片落地窗往外看,我們還在昨天被載來的別墅,這間房間空落落的,鋪了淺色的木地板,牆上油漆潔白如新,但這裡什麼傢俱都沒有,死寂的不像人住的地方。
「菜鳥們!歡迎加入拉格斯靈修會!」穿著黑斗篷面相兇惡男人拎著鞭子拿著平板電腦走進寬敞的房間。
他二話不說,用平板播放我們看過宣示入教的影片,我們在鏡頭前一絲不掛,醜態百出。
「這是違法的!」
「開什麼玩笑……」
「這是惡作劇嗎?太惡劣了。」
大家驚慌地抓緊斗篷,向陌生男人抗議。
他用手上的鞭子鞭打地板,厲聲說:「閉嘴。」
鞭子抽在地上的響聲不像在開玩笑,我們才知道對方不是虛晃的恐嚇,也不是惡作劇,對方認真的做著荒唐的事。這太可笑了,但沒有人笑得出來。
我懷抱微弱的希冀問:「我……可以退出拉格斯靈修會嗎?」
「如果你不怕影片被散播出去,能跑出這棟別墅,你可以離開。」他呲牙,不懷好意地笑:「我鼓勵你試試看,好久沒玩過貓捉老鼠的遊戲……」
跑不了的。
這場鬧劇無比認真的上演,我無法停止它,我們五個對彼此並不熟悉,倉促之下,我沒辦法說服大家一起反抗對方。
「我想回家。」程至臻哭著縮成一團。
「可以啊,等你乖乖的成為正式的靈修會教徒,你就可以從靈魂到肉體,由內而外的自由!」
瞎話。
怎麼辦?
好想逃走,但手腳都沒有力氣。
昨天還興高采烈想加入靈修會的王海威比所有人都快冷靜下來,他問:「你是誰?」
「這是個好問題,你們可以叫我凱薩,這是安琪菈導師給我的名字,對我的稱讚和期許,我會成為偉人
,在歷史揚名——」凱薩說到一半,不能忍受程至臻的抽泣聲,兇惡地說:「再哭我就抽妳。」
程至臻嚇得打了一個嗝,捂著嘴巴滿臉驚恐。
凱薩滿意她的反應,傲慢地頷首,發表言論說:「親愛的兄弟姊妹,我們之間是平等的,要彼此互助,彼此相愛——當然,這些優待是有前提的。你們學過的心靈成長課程不過是粗淺功夫,真正必須學會冥想,按部就班完成靈修會必須修習的功課,等你們體悟到拉格斯真力,我會真的把你們幫做兄弟姊妹。現在的你們只是羔羊,你知道什麼是羔羊嗎?」
鞭子指向程至臻,程至臻慌張地搖頭。
「你們必須奉獻自己,成為拉格斯、成為萬物之源生命之水的祭品,修行的足夠虔誠的人,就可以像導師們一樣獲得真力。」凱薩說。
一直縮在一邊沒說話的趙孝文小小聲地提問:「什麼真力?超能力?」
我對趙孝文沒什麼特別的印象,平常不太愛和同學交際,但要說他是怎麼樣的人,馬上就會想起他對心靈成長課程的狂熱,讓人印象深刻。
凱薩驕傲地說:「比如我,獲得天生神力的能力,這就是水主川導師為我點悟而領悟的真力。」
趙孝文顯然被他所說的吸引,追問說:「還有什麼樣的能力?」
王海威也提問:「錢大鑫導師和安琪菈導師有什麼樣的能力?」
「錢大鑫?錢大鑫只會賺錢,賺錢算得上什麼能力?只有你們這些菜鳥會崇拜他。」凱薩先是不屑,然後挺起胸膛自豪地說:「擁有力量才是一切,或者像安琪菈導師,她的美貌和身材還有交際手腕就是拉格斯賦予他的天賦,如果在古代,她就是傳說中的洛水女神再世,沒有人能比得上她。」
「冥想要怎麼做?」李賢斌問。
趙孝文、王海威、李賢斌,他們竟然相信凱薩。
他們比我還瘋。
「想學可不是動動嘴巴就能學到。」凱薩輕輕揮舞鞭子,看我們露出害怕的樣子,哈哈大笑,「首先得先磨磨你們的肉體,為靈修會盡心盡力!走吧,我帶你們去拿鏟子。」
鎧薩帶我們去工具間拿鏟子,一人一支,還讓我們拿畚箕和竹簍。
走到在別墅一小片相思樹林的後方,有一個挖到一半的坑,凱薩指著坑說:「我們要挖出拉格斯聖池,前頭別墅本身有的游泳池太匠氣了,一個真正靈驗的拉格斯聖池需要靠信徒們親自動手,挖坑排管線貼壁磚,到時候周圍的一草一木也要精心規劃——」他興致高昂地講的口沫橫飛,像我們展望未來,我沒想到看似兇惡沒腦子的傢伙口才竟然這樣好,連躲在後面不敢靠近的程至臻都因為看到未來美好可能,忘卻害怕,與我們貼近距離。
我希冀其中有人演戲,如果腦袋清楚的人只剩下我……
我問:「要挖多大?」
「一百米乘一百米,十公尺深——」凱薩說:「你們要相信自己,你們辦得到。」
不,這輩子沒人做得到,我一看就知道這裡的空間不可能挖出規整長寬一百米的正方形空間,頂多長六十,寬三十五至四十間。
「我的力氣很小……」程至臻說:「力氣小,挖的少的話,會不會得不到拉格斯真力?」
凱薩笑了,篤定地回答:「當然不會,重要的是竭盡全力。」
✠
這份工作和想像中的一樣辛苦,甚至辛苦數十倍。
每天四點天濛濛亮就起床,我們輪流做早餐,晚上暗得沒辦法挖坑,就回別墅用玻璃珠排磁磚花紋,把象徵水的符文拉格斯畫在磁磚上,還得點綴花樣,畫好了再送進烤爐燒。凱薩不停催促我們趕工,燒瓷磚的道具是租借來的,為了省錢,我們能越快完工越好。
食物每天都是水煮的地瓜或馬鈴薯,一人一天可以吃三個到五個,除此之外,冰箱裡沒有其他食物,洗澡的熱水器時好時壞,就算感冒也沒辦法休息。
睡覺時間至少過十二點,每天都四個小時或四個小時不到,又餓又累又病,倒下了還會被凱薩用鞭子抽醒……
真正的噩夢。
接下來對時間的感受好像被剝離了。
疲倦影響我的眼睛,我後來再也沒找到機會看時間,我不確定是不是凱薩把時鐘拿走了。
也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和他強調「人必須要有充足的睡眠,不然會死」這件事,被凱薩厭煩,乾脆把唯一的時鐘帶走了?我不確定。
再往後我更不記得過了幾日。
疲倦會致使免疫力下降,王海威和程至臻都感冒過,程至臻還發燒了好一段時間,我沒被他們傳染感冒的病菌,但我的情況卻比感冒還糟。
我從來到這裡那一天開始被迫停藥。
抗憂鬱的藥物可以慢慢減藥,不能隨便停藥,我長期使用那些藥物,突然停藥對我的影響非常大。
最開始兩天,迷幻藥的後遺症還存在著,眼前出現幻覺,我看見光,像在雲端之上,每踏出一步都輕飄飄的。所以再來幾天出現頭暈、手抖的狀況,我把些著症狀當作迷幻藥的後遺症。
直到暈眩感越來越嚴重,且無時不刻感受到嘔吐感,連續數夜模糊不清破碎的惡夢,伴隨強烈的焦慮感……
——我們全都是有某些地方扭曲,歪斜,不能順利游泳,會一直往下沉的人啊。
彷彿聽見直子站在我面前對我說,她穿著黑色的長裙,頭髮剪得短至耳下,瀏海齊眉,唇上有薄薄的口紅。
在直子的身後,有一大群雲朵般的白鯨,在如海水般湛藍的空氣中迴游。白鯨群越游越遠,我感到孤單,和強烈的被遺棄感。
我應該跟上,那是我的歸屬,白鯨應該和白鯨待在一起……
不,不對,我不是白鯨,而直子則是書裡的角色。
即使村上春樹《挪威的森林》銷量再好,再怎麼受歡迎,直子永遠都是一本書裡的虛擬角色,她不會活生生的出現在我眼前,就像白鯨也不會真的在空氣中自在地游。而且直子說的話缺了一半,她不該拿這句話問我,她該去問和她有關的人。
可是我看見的直子不像活生生的人,她更像機械或人偶,毫無感情地宣讀我的命運。
我會一直往下沉。
往下沉。
到深淵。
在深淵裡像拉格斯靈修會這樣扭曲的組織,到底聚集了多少不同尋常的扭曲人物?我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定義正常。
正常是一個模糊的概念,即使我狀況最好的時候,我也不算普通的正常人。
那些像凱薩一樣深信拉格斯靈修會的神異,他們不再正常,但卻好好地活著,體面的活。他們甚至將超負荷的勞力工作當成苦修——如果這不是我的幻覺,我確實看到將近十幾人和我們一起投入勞作,扛著鋤頭來挖拉格斯聖池——並帶領我們呼喊口號:「感恩拉格斯!讚嘆拉格斯!偉大的神聖水主川導師,請您叫我不畏險阻!我們願奉上一切尋求拉格斯的真義。願榮耀歸與拉格斯,生命之源,萬物之母!」
恍惚間,我們所有人排成一排,依造讚美的節奏鏟土,揚起大片飛灰。
白鯨群們高高低低的叫聲在耳廓裡繚繞。
回家,快回家。
跟我們來。
凱薩赤裸著上身,把斗篷為在腰間,一樣拎著皮鞭在相思林後的空地監工。
「那邊那個廢物!給我動起來!」凱薩暴躁地彎折手裡的皮鞭。
所有人左右張望,只有屈過庭呆呆的站在原地,握著鋤頭動也不動,他瘦削的身體包裹著黑斗篷,斗篷沾滿濕泥,包括他在內的所有人都逃不開這種狼狽。
「屈同學!」程至臻小聲叫他,想讓他快點動起來,至少別讓凱薩覺得屈過庭偷懶。
程至臻的聲音在一片寂靜中很明顯,凱薩瞪向程至臻,她嚇得快哭出來了,讓她冒險提醒的人卻還是沒有任何反應。
天空下起了毛毛細雨,相思林彷彿環繞一層霧氣,挖掘深坑的人在流汗前,就會被細細綿綿的雨水浸透,陰雨天讓人心壓抑,難以呼吸。
凱薩揮鞭,直接一鞭抽到屈過庭的後腦勺上,他一聲不吭,直接倒地,臉埋在濕泥裡。
其他人屏住氣息,害怕凱薩會將鞭子抽到他們身上,凱薩看屈過庭的臉埋在濕泥一動也不動,又打了屈過庭一下,「裝死?你敢裝死?」
屈過庭的身軀反射性地顫動,然後又恢復平靜。
看起來像真的死了。
凱薩不想鬧出人命,他指使其他人去把屈過庭翻個身,看他到底在搞什麼鬼。凱薩註定得不到任何結果。
從這一天開始,白鯨群呼喚屈過庭的聲音就再也沒停止過。
無論醒著,或在夢裡,白鯨們都在喊他離開。
屈過庭也想離開,但沒有人能離開,最後他連想逃跑的餘力都失去了。
時間變得沒有太多意義。
一秒、一天、一小時,有時差不多長,好像永遠都持續如此,有時差不多短,一晃眼,挖掘聖池的工作好像就要結束。
那不是一個標準大小的正方,反而是沿著樹林挖掘出的不規則深坑,最淺的地方都有兩米。
好像失去靈魂,屈過庭現在只會一個指令一個動作,沒人喊他他可以不吃不喝發呆一整天,對話語的反應還特別遲鈍。
偶而,他嘗試用鏟子傷害自己。
從腳背、小腿、腹部都留下淤青和血痕,他們使用的鏟子不夠鋒利,屈過庭試圖劃開脖子殺死自己的舉動不可能成功。
「屈過庭是被邪靈侵入的人。」
「他需要更努力來擺脫邪靈。」
「讓他浸泡在水裡,提前洗禮。」
屈過庭被沉入別墅前頭的泳池裡,消毒水獨特的氣味湧入口鼻,他無法呼吸,但他因此更清晰地聽見鯨群的私語。
原來他擱淺了。
——你擱淺了?
原來他沒力氣游了。
——你離我們太遠了,我們救不到你。
原來他會死。
——你再不趕上我們,你真的會死。
游不動的鯨魚,被困在水裡,沒辦法回到空氣中自在呼吸。
原來如此。屈過庭釋然。
原來天上的不是白雲,是屬於我的白鯨族群,我再也追不上他們,於是我被困在水裡,成為擱淺的鯨魚。
TBC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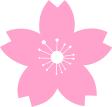
和我聊聊⋯⋯